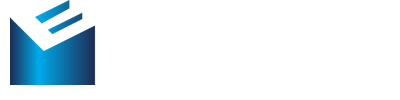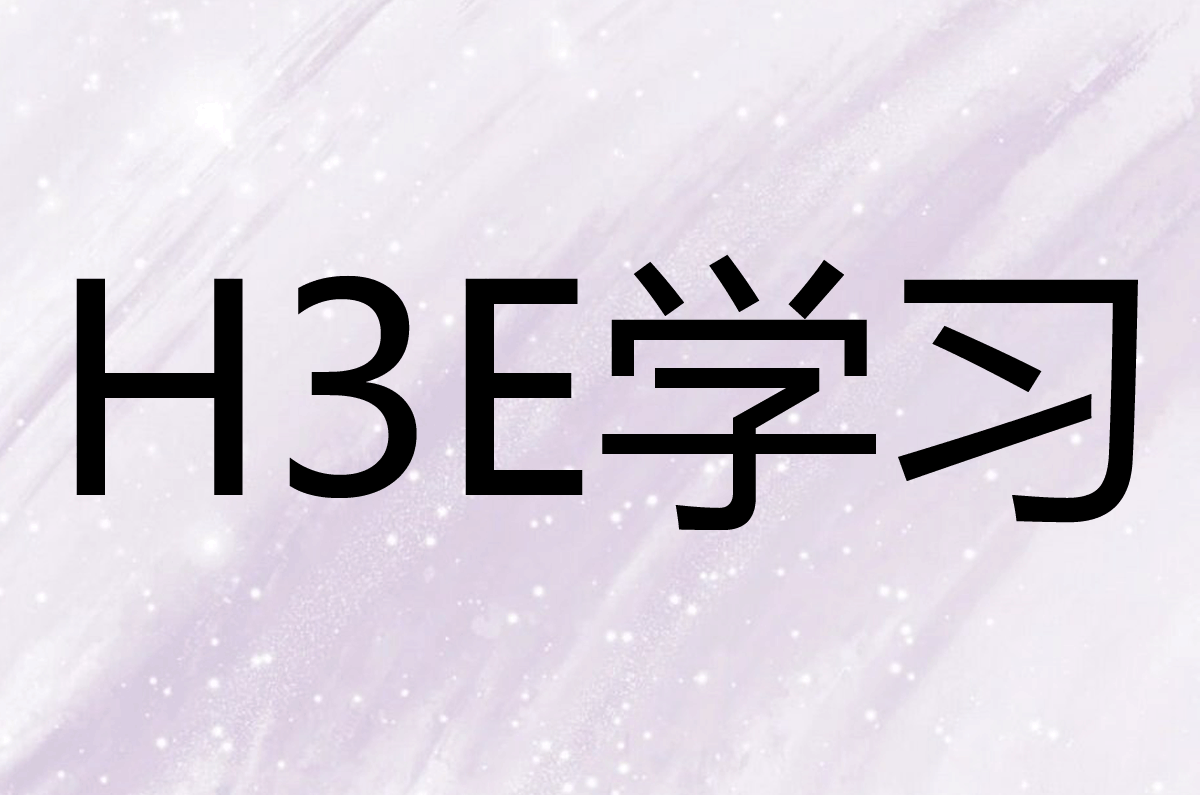类比是一种什么推理-类比是一种 什么推理

类比是一种比喻性的推理,它将两个或多个不同的事物进行比较和对比,以便更好地理解和解释它们之间的关系。类比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复杂的思想和概念,并从中得出新的洞察和结论。
类比是什么(语文)
所谓类比,就是由两个对象的某些相同或相似的性质,推断它们在其他性质上也有可能相同或相似的一种推理形式。类比是一种主观的不充分的似真推理,因此,要确认其猜想的正确性,还须经过严格的逻辑论证.
类比是一种主观的不充分的似真推理,因此,要确认其猜想的正确性,还须经过严格的逻辑论证.对比,是把具有明显差异、矛盾和对立的双方安排在一起,进行对照比较的表现手法。写作中的对比手法,就是把事物、现象和过程中矛盾的双方,安置在一定条件下,使之集中在一个完整的艺术统一体中,形成相辅相成的比照和呼应关系。运用这种手法,有利于充分显示事物的矛盾,突出被表现事物的本质特征,加强文章的艺术效果和感染力。对比是把对立的意思或事物、或把事物的两个方面放在一起作比较,让读者在比较中分清好坏、辨别是非。这种手法可以突出好与坏、善与恶、美与丑的对立,给人极鲜明的形象和极强烈的感受。
谈《为了忘却的记念》的类比手法
茅盾先生1941年10月16日作《最理想的人性——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五周年》。该文用一句话概括鲁迅毕生的文学事业——“拔出‘人性’中的萧艾;培养‘人性’中的芝兰”。《为了忘却的记念》中提到的五位“中国很好的青年”,该是鲁迅“培养人性”中最出色的几棵“芝兰”吧。这五株“芝兰”之所以有如此强烈的感召力,我以为与作品恰当的类比手法不无关系。
柔石“台州式的硬气,颇有点迂,有时会令我忽而想起了方孝孺,觉得很有些这模样的”。这是文章的第一次类比。方孝孺是一个固执的具有正义感的人,因为不肯替燕王朱棣起草即帝位的诏书而被杀害。燕王威胁道:“你不怕诛九族吗?”方孝孺豪迈地说:“即诛十族何妨?”当缚其弟孝友至,他潸然涕下。孝友作诗曰:“吾兄何必泪潸潸,取义成仁在此间。华表柱头千载鹤,旅魂依旧到家山。”方氏家族被杀数百人。这段文字表现了方孝孺、方孝友兄弟宁折不弯视死如归的硬骨头精神。“台州式硬气”,并非专指孝孺一人。鲁迅只提到他的名字,不过以他作代表罢了。方孝孺深深地知道顶撞皇帝是要砍脑袋的,燕王已明确告诉他:“诛九族”。他毫不在乎地说“即诛十族何妨”,使亲友做了无谓的牺牲,这确实“颇有点迂”。朱棣主政,“以剥皮始,以剥皮终”(《病后杂谈》)而“闻名”天下,鲁迅用孝孺类比柔石,以朱棣类比独夫蟊贼蒋介石,虽没有明指蒋介石“以剥皮始,以剥皮终”般凶残,但懂得历史的读者,看了这个类比,蒋介石何等人也,也就不难想见了。这就是“台州式硬气”要告诉我们的内容——这无异给国民党当头一闷棍,无情地撕下了他们的假面,让他露出刽子手青面獠牙的真相。
再看第二个类比。当作者受到反动派追踪,通缉,作品引用了《说岳全传》里高僧坐化的故事。高僧即道悦和尚,他力劝岳飞出家,免遭秦桧毒手。这便触犯了当时不成文的法律,被官方捉拿。“当追捕的差役刚走到寺门之前,他就坐化了,还留下什么‘何立从东来,我向西方走’的偈子”。这一方面说明了被捕者的无辜,控拆了当权者的可耻,另一方面,作者明确地宣布自己的斗争方式:“我不是高僧,没有涅盘的自由,却还有生之留恋,我于是就逃走”。“逃走”是反语,是“壕堑战术”的形象化,“打仗就要象打仗”,“这不是小孩子赌气,要站稳自己的脚跟,躲在自己的壕沟里,沉着的作战,一步步前进。”一个“躲”字,形象地说明与国民党作战,必须有坚韧的精神。要保存实力,不做无谓的牺牲。“如果敌人用激将法说‘你敢走出来’,你居然走了出来,那么,这就象许褚的赤膊上阵,中了箭是活该。而笨到会中敌人这一类奸计的人,总也不肯,也不会韧战的。”(瞿秋白《鲁迅杂感选集序言》)这段话正是鲁迅对敌作战以退为进的具体表现。
为了讲清鲁迅的“壕堑战术”、“韧”的精神,《两地书》里有两段话说得很精辟,其一是:“在进取的国民中,性急是好的,但生在麻木如中国的地方,却容易吃亏,纵使如何牺牲,也无非毁灭自己,于国度没有影响。”(《鲁迅全集》)第十一卷46页)其二是:“所以我想,在青年,须是有不平而不悲观,常抗战而亦自卫,倘荆棘非践不可,固然不得不践,但若无须必践,即下必随便去践,这就是我之所以主张‘壕堑战’的原因,其实也无非想多留下几个战士,以得更多的战绩。”(《鲁迅全集》第十一卷21页)
这两段话把鲁迅“我不是高僧……我于是就逃走”的心思和盘托出了。从而在读者面前耸起一座巍峨的丰碑:智勇兼备的英雄形象——鲁迅!
第三个类比,即用德国进步的版画家比拟作者,鲁迅为了纪念失去的“中国很好的青年”柔石、白莽,为了表达对柔石母亲的无限敬意和景仰之情,在《北斗》创刊时,选了一幅珂勒惠支夫人的名为《牺牲》的版画登出来,“是一个母亲悲哀地献出她的儿子去的”。鲁迅十分尊敬这位革命母亲,对她失去儿子柔石表示深切哀痛,“大小无数的人肉筵宴,即从有文明以来,一直排到现在,人们在这会场中吃人、被吃,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……扫荡这些食人者,掀掉这筵席,毁坏这厨房,则是现在青年的使命”。(《灯下漫笔》)是的,只有起来斗争,才能拯救中国,只有化悲痛为力量,猛烈攻击这群食人者,才能结束这苦难的历史。
这个类比,是用版画家类比作者,用版画中“悲哀地献出她儿子去的”双目失明的母亲,类比柔石双目失明的母亲,用那“献出去”的儿子比柔石。然而木刻中“双目失明的母亲”尚知道“她的儿子”已经“牺牲”,而柔石的“双目失明”的母亲,“还以为她的儿子仍在上海从事翻呢!”作者强调指出:“算是只有我一个人心里知道的柔石的纪念。”意思是他的——革命的母亲仍蒙在鼓里,这真是莫大的悲哀!作者心头的悲哀,中国社会的悲哀,透过这幅木刻全说清楚了!
第四个类比,用斐多菲《生命与爱情》的思想境界比拟革命者白莽即殷夫的革命高于一切的伟大品格。诗人以生命、爱情、自由三者之间的抉择,突出他酷爱自由的性格,不自由毋宁死的强烈感情。用生命与爱情来烘托自由的珍贵,意义多么深刻。在一个被奴役的国家里,肯定能引起失去自由的人们强烈的共鸣。这首诗从匈牙利走到中国,证明它有多么大的普遍意义。诗人写下这首诗,不自觉地在制造自己的形象,不是用色彩和线条,不是用文字描绘,而是凭直抒胸臆的感情来显示。一个来去无牵挂,光明磊落的革命志士的高大形象从壮怀激烈的境界中升起!这诗中的形象就是斐多菲!就是殷夫、柔石、胡也频、李伟森、冯铿!作者在第二节里提到的“无论从旧道德、从新道德,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事,他就挑选上,自己背起来”。这样的好青年,“他的身上,中了十弹!”难怪作者要质问,要怒吼——“这是怎样的世界呢!”
第五个类比,鲁迅在不能继续写下去的悲愤中,引用了《思旧赋》:“青年时期读向子期《思旧赋》,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,刚开头却又煞了尾,然而,现在我懂了。”这是何等复杂而真挚的感情。《思旧赋》是魏晋时期的文学家向子期的作品。他的好友嵇康、吕安被司马昭杀害后,他悲愤地写下这篇文章来纪念他们。由于当时处在司马昭政权的高压下,不能畅所欲言来表达自己的哀思,文章写得短而隐晦,这种无法写下去的情感和鲁迅当时“吟罢低眉无写处”的心境多么相似,鲁迅在这苦难的,梦一样的日子里想起了向子期。这是用向子期比自己,用司马昭比蒋介石,用嵇康、吕安比五位被暗杀的青年作家。
作者心里尽管悲愤,社会尽管黑暗,但作者深深地知道:“快了!一个政权到了对外屈服,对内束手,只知道杀人,放火,焚书,掳钱的时候,离末日也就不远了。他们分明感到:天下已经没有自己的份,现在是在毁别人的,烧别人的,杀别人的,抢别人的。越是凶,越是暴露了他们卑怯和失败的心理。”(唐弢《琐记》)。因此,作者说:“我不如忘却……但我知道,即使不是我,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,再说起他们的时候……”
声明:本站所有文章资源内容,如无特殊说明或标注,均为大数据处理内容。如若本站内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权益,可联系本站删除。
原文链接:https://edu.h3e.cn/edu/54961.html